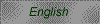<目錄頁>
禪 宗 思 想 問 答
釋界靜(仁寬)著
禪宗的最大特色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是不執文字的意思;教外別傳,是不著教相的意思。不執文字,不等於離開文字;不著教相,不等於無須教義。離開文字教相是禪;應用文字教相也是禪,所以在禪的本質上既無獨斷的教義也無所依的經典;但卻包含著一切經教和文字。為了修學方便,於是寫作此一禪學問答。
禪的思想根據
一、禪宗思想問答──《維摩詰經》問題集
1、問:禪宗與三論宗一樣「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無智、無得、無念、無心、無住、無著、無依、無生等思想理論同樣依據何經?如何問答?
2、問:《維摩經•弟子品》第三,有哪一段話作為三論宗和禪宗的所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理論根據?
3、問:維摩居士對誰說的一段話成為禪宗祖師「不以一法示人」的理論根據?三論宗祖師對此有何說法?
4、問:禪宗主張「生佛同性、迷悟不二」的要旨出自《維摩經》何品?如何說?
5、問:禪宗主張「佛法不離世間法」的妙諦出自《維摩經》何處?如何說?
6、問:禪宗也主張「一切諸法是解脫相」的理論根據何在?
7、問:禪宗與三論宗一樣依教修觀,在修證上有個共同觀念,那便是「不可得處,怎麼得」的修證消息。這種思想根據何在?
8、問:禪宗的「唯心淨土」、「直心是道場」思想出自何處?
9、問:禪宗的「娑婆即淨土」的思想根據何處?
10、問:禪宗認為眾生的法身不可說;法身遍一切處;法身是「動靜一如」等思想有何依據?
11、問:禪宗的「默識心通」的無言妙用根據何在?
12、問:禪宗認為要達到「自在無礙」、「徹見本性」、「法我不二」、「人法不二」以致於現實地打開常、樂、我、淨的涅槃四德心境,必須是對「無」的體驗,也就是自己的根本意識,從差別而進入平等的體驗,然這種體驗必須對於「法」或「真如」的把握,而這「法」或「真如」是不能形相加以把握的,這就是對「無」的體驗。這種「無」的根本指導思想出自《維摩詰經》那一段話?如何解說?
13、問:禪認為「法身」是不病的,感覺有病痛是生滅法的「色身」。若能超越形象的覺受,病就不影響「法身」的自在。禪宗祖師對此有何垂示?有何經典可以說明這一教示?
14、問:真如有隨緣與不變二義,禪宗在真如二義上重視什麼?禪宗祖師如何教示?有何經文可以證明?
1、問:禪宗與三論宗一樣「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無智、無得、無念、無心、無住、無著、無依、無生等思想理論同樣依據何經?如何問答?
答:禪宗與三論宗一樣「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思想主張,這種思想理論同樣根據《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第七,文殊師利與維摩居士的一段對話: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所謂「無住」就是無所住著,就是真如,這真如就是在顛倒妄想還未生以前,也就是禪宗說的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也如同儒家所說的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的情狀。這真如無所寄託,所以叫「無住」。
真如既然是無住,當然就不能有根本,有本就有住了,只有無本才能為萬物之本,所以說從無住、無本才能立一切法。
無住有兩種:一是真如無住;二是無明無住。真如無住是真實不虛,是一切清淨善法的根本;無明無住是虛幻不實,是一切染污惡法的源泉。
真如無住就是法性,即真如法性徧滿虛空,無有住處。《金剛經》說:「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住生心的心就是真心。真如既然是一切法的體性,而體性無所依住,所以叫無住。但是若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說。那麼這真如無住就能為一切善法建立的根本了。
無明無住就是心動,心動就有顛倒想,顛倒想就是虛妄分別,有虛妄分別就起貪欲,有貪欲就有身,有身就會造善惡業,那這無明無住就能為一切染法建立的根本了。所以
唯識宗說「真如是迷悟的總依,染性依之迷生;淨性依之悟起,一切染淨諸法由之建立」。
有關真如問題,有幾點略加說明,一、佛教與外道對真如的不同主張;二、真如的情狀為何物?三、真如的異名;四、真如在心理、空間、時間上的不同名稱;五、六祖對真如的具體應用。
一、佛教說真如只是為一切法依;而外道卻說真如能生一切法。如說:
「若外道云能生一切;我之真如非能生故,但為法依,故言無住立一切法,不言生也」。
在這裏依與生的意義大不相同,如果說真如能生一切法,這真如成生滅,因為有生就有滅;而實則真如是不生不滅的,因為真如即是一切法的法性,而法性遍滿虛空,無有住處,所以叫「無住」,這無住即真如,這真如即無為法,所以叫「真如無為」。這真如無為只能是隨眾生迷悟因緣,「染性依之迷生;淨性依之悟起,一切染淨諸法由之建立」罷了。
二、這「不生不滅」的真如或稱「本來面目」的情狀,到底為何物?三論宗說「開口即錯,動念即乖」;禪宗說「說似一物即不中」但我們可以鏡子為例:鏡子,它永遠保持著本來明亮而不會被任何反映其中的外物所蒙蔽。這便是惠能大師得法偈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中的「無一物」。這「無一物」就是「禪」,要問「禪」是什麼?即所謂「說似一物即不中」。
三、六祖的「無一物」就是「禪」,禪就是真如,亦名佛性、法性、實際、實相、法界、如來藏、法身、心性、如如、如實、自性清淨心、一心、無住等。如三論宗吉藏大師的《大乘玄論》卷三說:
「經(大般涅槃經)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實際等,並是佛性之異名。何以知之?涅槃經自說佛性有種種名,於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若、一乘,亦名首楞嚴三昧、師子吼三昧。故知大聖隨緣善巧,於諸經中說名不同。故於《涅槃經》中名為佛性,則於《華嚴》名為法界,於《勝鬘》中名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楞伽》名為八識,《首楞嚴經》名首楞嚴三昧,《法華》名一乘一道,《大品》名為般若、法性,《維摩》名為無住、實際。如是等名,皆是佛性之異名……」。
吉藏大師說佛性在《楞伽》名為八識;然也有稱「真性」的。如同經說:「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又佛為度外道將佛性稱為「我」義,如《大般涅槃經》卷八說:
「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以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大12•648中)
四、達摩祖師依《楞伽》常稱佛性為「真性」,到六祖惠能大師常稱「自性」或「本性」。有時跟真如一起連稱,如說:「真如自性」;「真如本性」。
這「真如本性」盡管被時空所限制,並且也服從自然法則。但是它仍然保留著本來面目而不動。這本來面目的真如本性,從心理上看,可以稱為「無念」,是說我們所有的心念和感覺都來自「無意識」,而這個無意識就是「自性」或稱「心體」。從空間上看,稱為「無相」,因為它是無為法,是無造作的;是法身,是無形相的。從時間上看,可以稱為「無住」,因為它永遠在明亮當中,我們如果沒有它(自性),那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所用的這個世界又會崩潰。所以自性就是般若,這叫「自性起用」,或「真如起用」,然自性是體,般若是用。
五、從六祖惠能大師得法偈看,他是根據徹底頓悟自己心性來說的,他遮破菩提,否定明鏡。這越是否定到極處,越是有大肯定的意義在,所以後人對這「無一物」更展開地說:「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臺」。這正是符合《維摩詰經》的「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思想根據所在。
惠能大師對真如的具體應用,是在教禪人修禪的實踐方法上的法門。如《壇經.疑問品》說:
「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於諸法上,念念不住」。
1、「於相而離相」即是破我執、法執的說明。行者內觀我空,外觀法亦空,若證我空法空,即得空慧,有空慧的聖者,對一切相才能真正做到「於相而離相」。如《金剛經》說:「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能離一切諸相,即是「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智」的聖人了。
總之,若行者常離一切相,即把握客觀諸法的真實體性,這就是「無相為體」的說明。
客觀諸法的真實體性是平等無二無別的,如《壇經.機緣品》說:
「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
這就是平等無二性的說明。
2、「於念而無念」是說:我們對一切境(六境)上,心不起執著叫無念。當我們人心對一切境時是念,若能做到心不執著,就是無念。所以稱「於念而無念」。即所謂「於諸境上心不染」就是「無念」的意思。《般若品》也說:「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
3、無住者,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和「無住為本」的「住」是執著的意思。修一切法門,同樣都是要拋開執著,執著是生死的根本,不執著是修行的根本,所以叫「無住為本」。六祖聽到《金剛經》「不應於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這無住生心是修行的根本目標。有人聽佛讚歎彌陀淨土,就執著極樂淨土,欣喜莊嚴國土;聽佛說娑婆五濁惡世,就生厭離心,不知這是佛的方便誘導法門。如此修行,一無是處。常被境轉故。不知淨土當淨自心,不知彌陀只在自性中。六祖說: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
對於「無住」《壇經》中又一處提到:
「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
以上五點,只是對真如無住的簡略說明,從這可以知道三論宗與禪宗在思想理論上的共同處,也從這一問答更容易掌握三論宗的中道佛性義和禪宗的佛性思想以及修行的「無住為本」目標。
2、問:《維摩經•弟子品》第三,有哪一段話作為三論宗和禪宗的所謂「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理論根據?
答:《弟子品》說:「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煩惱是生死的因;涅槃是修道證得;聲聞乘人以為有實性的煩惱可斷,有實性的涅槃可證;菩薩了達煩惱性空,煩惱當體即是涅槃,不須在煩惱外另求取涅槃,所以菩薩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的。
這「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和《菩薩品》說的「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這真是「一切現成」的「頓教」理論根據,只有一切現成,「頓悟」才有可能,也只有一切現成才能把修持法門貫徹在日常行持中去。只有愚智佛性無二,煩惱即菩提的無得正觀般若現前,才能「見諸佛境界」。對此,六祖的《壇經•般若品》說: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六祖強調無念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反對百物不思的邊執見,這正符合佛說的《般若經》、《維摩經》和《大智度論》等空性般若教理融貫到日常行動方面上來實踐。
所謂「煩惱」,就是「心煩意惱」。人之所以感受到心煩意惱,是由於一種樂感的「無明無住」的意志反射作用而現起的。如前面第一個問題中說過的:人必有身,身以貪欲為本,貪欲以虛妄分別為本,虛妄分別以顛倒想為本。可見,人是依於自身的意慾盲目地「虛妄分別,顛倒妄想」衝動而發生的「煩惱」。那麼:
人是否就這樣永遠被自身的無明意志作用驅使下去呢?如果我們完全認定了這煩惱永遠是定性煩惱,那解脫就不可能了。可是,人同時也潛伏在自身深處的「真如無住」的真實合理的意志,一旦發見到而起作用時,這就被稱為「菩提」了。「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其意就在這。也是「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的頓教說明。所謂真實合理的意志起用,即六祖說的「真如起用」即是佛用同義。
人的習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記得大約十年前左右《世界日報》登著這樣一個事實。有一美國白人,俱生帶來的習性就是喜歡吃羊肉;有一天,他到一家專門買新鮮煮熟的羊肉店,做在小餐桌正等著吃羊肉,此時窗外正好有一隻羊正在一口一口地吃著新鮮的草,他看得入神,開始觀察覺照。羊這麼可愛,牠吃草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生命嗎?可是牠還有幾個時辰生命呢?人為什麼吃掉牠類的生命而養活自身呢?羊只是吃草就可養活生命呀!用六祖的話,他是「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他明白了,他把這餐未入口的羊肉錢放在桌上離開了羊肉店。
原來他是自己開一家工廠的總經理。次日當他上班時,便招集工人宣布說:我從今天開始不吃葷,你們在家吃不吃葷我管不著,但從明天開始不許帶有葷的便當來上班。如果不聽這一規定,從明天開始就不要上班了。
在西方國家的美國,給工人做這種規定,可說是圍背了上帝的旨意,因為「羊是上帝造出來給人吃」的。但他「用自真如性」,做到「邪正兩不用,清淨至無餘」的真解脫境,這種解脫境,不受上帝和任何的約制,可謂達到「禪」的人生自由生活。
再說六祖強調的無念行的思想,也是根據《維摩經》。如文殊問維摩:「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這「正念」即「無念」,「無念」即「無心」。於何處無心呢?於「色、聲、香、味、觸、法六處(六塵)無心。
可見「無念」即無邪念的意謂,也即無染雜意念的意思。這種「無念行」也即要求將第七末那識轉成平等性智的意謂。
坐禪除了調身、調息外,最根本的是在於調心。調心法可分曹洞、臨濟兩派,見解不同:曹洞為坐禪的調心,在調第七識以明染污心;臨濟為見性的調心,在調第八識以見真如性,見性的調心,主要在參「無」字的公案。如狗子無佛性的話頭等;坐禪調心有一要術說:
「思量箇不思量的,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呢?非思量即為坐禪之要術也。」
「思量」即「思慮量度」的簡稱,即有第七末那識,是有心;「不思量」是無心。偏於有心既然成病;那麼偏於無心也是成病。現在,不涉於有心的思量;也不沉於無心的不思量,以超脫了散亂與昏沈的當體,便叫「思量箇不思量的」。那麼,「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呢」?那就是「非思量即為坐禪之要術也」。非思量的「非」字在這裡不是否定義,是指坐禪上的「正念」,即「無心」、「無念」的超有、無、男、女、邪、正等的二元對待。既離造作之念,又不是「百物不思」的狀態。這種坐禪上的「正念」即是「正思維」。正符合於「禪那」的「思維修」的原意。「禪那」有「反省」的意思。也就是說心尚存有煩惱與菩提、生死與涅槃、凡夫與佛、迷悟、斷證等相對立的染雜心念在,那就是染污的有念行;六祖強調的無念行意即要人離迷悟,越凡聖,念念須正,心心皆非染污的心行。如有僧曰:
「臥龍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對此六祖便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怎麼長?」
用三論宗吉藏大師的話說:那僧人的心境如「步曲蟲,捨一取一」。捨生死取涅槃;斷煩惱證菩提。所以六祖教示說:「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次就見性的調心來說:在臨濟宗認為公案和坐禪都是為了要達到佛的境涯的一種方便手段。不是坐禪即成佛。也就是說:首先依於坐禪,調整身體,再其次就是超越有無二見而體驗第一義空,換句話說即是發動真如自性起用,選擇千七百則中的其中一個公案,用來調心與見性。如趙州的狗子無佛性的公案來說:
-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無。」
云:「蠢動含靈皆有佛,狗子因甚卻無?」
師云:「為伊(它)有業識在。」
- 又一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師云:「有。」
云:「為甚麼入皮袋裏?」
師云:「知而故犯。」
趙州的這種答法,一說「無」;一說「有」。照理論上說是有矛盾,但在趙州的立場說,雖是同一問題而作不同的答案,卻不會有自語相違的。因為禪宗祖師回答問題時,常是以應眾生的根性接引學人,相應著提問人的立場不同而作不同答復。禪的教學方式不是要使問的人理解;而是要使問的人起疑,如答無佛性的原因,著重於因為它有「業識在」。有業識在雖然成為問題,而實際上成為問題的卻是答的「無」。這個「無」是趙州獨創的「無」,是禪的生命。參禪的人首先必須透過這個無的關門,因為這是開顯佛性的第一步。如無門關第一則說: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無門曰: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個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通身起個疑團,參個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盡平身氣力,舉個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狗子佛性,全提正令!才涉有無,喪身失命!」
所謂「心路」即指煩惱。依《成唯識論》說:心路的根本是第八阿賴耶識,譯為「藏識」。在善惡兩心未發的種子,就是藏在這個藏識當中。但是,即使是善的種子,也只是對著惡的種子而說的善,這種善不能說是純真的佛性。禪,就是要窮絕這根本的善惡種子的心路,再試著超越這善惡種子的藏識而躍向於「本來無一物」的大圓滿真如心。如此,即是用「無」的一刀,粉碎了從前的「惡知惡覺」;從此,開始了真如清淨心的活動。
原來我們的思維方式,一直停滯在將事物對立起來觀察;比較起來觀察。這種觀察法,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畢竟不是究竟的觀察法。
其實,一切事物都是獨立存在著,沒有對立的,一切都是超對立的存在。所以生也好,死也罷,原是一樣;既沒有與生相對立的死;也沒有與死相對立的生,這就是「生死即涅槃」的道理。可是我們一直將生死與涅槃對立起來思維,認為有個實性的生死可了;有個實性的涅槃可證。所以在禪的立場說,我們必須有改變這種根本的固有思維模式,反省「蕩盡從前惡知惡覺」,必須進入「斷一切諸有」的過程。必須超越「煩惱與菩提」的二元對立觀念,離卻一切形相,即達到實相的境地。到這才叫真解脫境,也叫獨脫無依、無住、無得、無寄情分別的佛的境涯。從此產生新的生命,過著禪的自由生活。
3、問:維摩居士對誰說的一段話成為禪宗祖師「不以一法示人」的理論根據?三論宗祖師對此有何說法?
答:《弟子品》維摩居士對大目連尊者說:
「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對此,三論宗的第八祖僧肇和吉藏大師都同樣說:「終日說而未嘗說,終日聞未嘗聞」的無聞無得才能真聞真得的佛陀說法本意。
所謂」法相如是」的「法相」是指「法性」。如說:「有佛無佛,法性常住」是指一切諸法的法相自從久遠以前已經本來就是如此了,雖千佛出世,想要為之增減一字,都不可能。這是自然界的法相本來如是真理,這真理不存在於經典中,所以禪宗祖師「不以一法示人」道理在此;也是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用意所在。如《碧巖集》第六中記載著須菩提與帝釋天的一段問答,意謂法不在經中,如說:
「須菩提岩中宴坐,入空三昧時,諸天雨花讚歎。尊者問:『雨花讚歎,復是何人?』答曰:『我是天帝釋。』『汝何讚歎?』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
在大乘佛教思想中,說「空」的真理,無過於《般若經》。然而經中所說的「空」,乃是語言強名相說,不是「空」的本身;同時這依俗諦的語言說和耳根聽聞的空,不是第一義諦的真空。所以說「第一義空,不可說」。說出來的還是未超越於「有」,因為語言說的只是概念所構成的假名──空。所以,第一義諦真空是超越了聞說,到達離一切名狀概念世界而「入空三昧時」,空才能如實地現前;因此,帝釋讚歎須菩提宴坐,「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如《金剛般若經》說的:「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可見聞說的皆非「真般若」,只是一種文字符號、概念而已。
又如禪宗的《指月錄》也有一則不講而講的故事:人稱他為善慧菩薩,即是有名的傅大士,生於西元497年,是一位出色的禪宗先哲。
有一次,梁武帝請他講《金剛經》,他登上堂後,拍了一下驚堂木,便下臺了,弄得梁武帝莫名其妙。
善慧問武帝:「你了解了嗎?」
武帝回答說:「完全不了解。」
善慧卻說:「但我已經把全部此經講完了。」
《金剛般若經》只是描述佛證悟的第一義空境界,這種「真空」是泯絕識情,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語言相;這種「真空」也正是「真般若」;也是前面維摩說的「法相如是」的「法爾真理」。這種法爾真理是「禪」的主眼,禪宗祖師「不以一法示人」其意在此。由此,也可知道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宗旨了。
「不立文字」的「不立」與「不用」,不可混同。對禪宗思想一無所知的禪宗門外人說:「禪宗的公案已經成為過去,那些陳舊的文字是無用的,為何還重提公案呢?」這種人根本不知道「不立文字」的真正含意,也根本不知道公案是禪的生命,是禪的經典,如果沒有公案作為禪的依據,禪就不能成其為禪了。所以,「不立文字」不等於不用文字。有些禪門中人,正因為將「不立」與「不用」混同,不但疏忽了經典的研究,甚至有漫罵教學者的傾向,更有那些在禪堂中終日參「父母未生前,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問他「父母未生前」的「父母」是指什麼?回答說:「這還要問嗎?當然是指今生的生身父母了」。這種不依經教而盲修瞎練的可憐蟲,不但誤了自己,也更誤了他人呢!但是另一些整天沉迷於經教名相的研究,這對達磨看來,也是可憐蟲:達磨祖師初來中國時,正逢研究經教注疏時代,於是獨標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旗幟。
文字只是符號而不是真理的本身,即使借著大量的文字來表達真理,但這僅是意義的表示而不是真理。經典中所說的「空」,並不是「第一義空」,這種真空般若不能依賴文字或語言可得相傳的。所以,禪宗祖師「不以一法示人」其意在此,也是「教外別傳」的說明。因此,古人將「教外別傳」解釋為「傳者契也」。
昨天,我在草地上教王昱海鋤草皮,從表面看起來,我以鋤頭法傳授與他,教他何謂鋤頭口?第一鋤頭從何處先下?何為翻草皮?草皮到何時才真正離地?如何聽覺草根?鋤後放到何處?只除一小片草皮有這麼多的文字符號。雖說是「鋤頭法的傳授」,但實際上,這種傳只可說是「不傳的傳」。除了心心契合給與證明他鋤頭法的正確與否之外,便「更無一法授人」。欲知鋤頭法如何?可到山莊問海蓮。
10/28/2003 寫於海蓮休閒山莊
4、問:禪宗主張「生佛同性、迷悟不二」的要旨出自《維摩經》何品?如何說?
答:出自《維摩經、菩薩品》第四說:
「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授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無退者。」
維摩結居士對彌勒說:你彌勒如果以為自己得到授記,那麼眾生也應該都得到授記,為什麼呢?因為「如」的定義是「不二」的,眾生和佛沒有兩樣,都具有真如理體,如《華嚴經》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悉有如來智慧德相,皆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又「如」的定義也是「不異」的,眾生和佛是平等無差別的,有所謂「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會中,無自他之形相」。
「一切眾生,即菩提相」的菩提在此可分為二:一是自性菩提;二是修得菩提。維摩居士以「自性菩提」來非難「修得菩提」的幻記。自性菩提是不從外得的;修得菩提是幻修的,幻修幻記的修得菩提也不能說是另從外得的。如果彌勒可得自性菩提,一切眾生亦應可以得的,為什麼呢?因為自性菩提是遍一切處的,一切眾生相,當體即是自性菩提的顯現。
涅槃,譯作滅度,新譯為圓寂,即達到不生不滅的寂滅狀態。依唯識宗說涅槃有四種:
一、自性清淨涅槃,指一切眾生法相的真如理體;二、有餘依涅槃,指煩惱苦因除盡所顯的真理;三、無餘依涅槃,指煩惱苦果斷盡所顯的真理;四、無住涅槃,指所知障已盡,大悲般若所轉的真理。這裹是以自性清淨涅槃來反難其他三種修證所得的涅槃。修證所得的涅槃,是幻修幻證的,既不從外得,也不從新生,所證得的也就是自性清淨涅槃。那麼,如果彌勒既得自性涅槃,難道眾生的自性就不是本具涅槃了嗎?為什麼呢?
因為諸佛知道一切眾生是畢竟寂滅的,眾生相就是涅槃相,不必更有眾生相的所滅,而另有涅槃相的所證。這樣,眾生相和涅槃相不二,彌勒是眾生之一!彌勒既得滅度,一切眾生亦當滅度。這就是眾生與佛真如佛性平等,懂得這道理,彌勒就不該以這漸次修行才得不退轉地的法門去誘惑諸天人!須知道,在平等的真如法性中,實無菩提心可發,因為眾生佛性本來具足;也沒有菩提心可退,因為眾生佛性從無遺失。
由此可見「生佛同性」的「性」是指佛性,眾生在迷流;佛已得證悟。從現象上觀察,迷悟有別,是二;然從體性上去體驗,那當體即是佛。六祖曾說「凡夫即佛」,也是從佛體性上講的,所以說「生佛同性,迷悟不二」。因為「一切眾生皆如」的緣故。
眾生是萬有中的一種,眾生既然如性平等,那麼,其餘的動、植物包括山河大地無不是如性平等,有所謂「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道理即在此。但在現實世界中,眾生有迷悟、垢淨之別;事物有生滅、成壞之對待;眾生與草木有覺與不覺之鑒別;一旦證到無分別智的大乘菩薩看一切事物就沒有任何寄情分別了。可見禪宗主張「生佛同性,迷悟不二」是站在平等無二、真如法性的無得、無念、無住的立場上講的。這種立場便是禪的根本法;這種無寄情分別之境是超越了一切迷悟、凡聖、是非、得失的清淨自由無礙之境,這即是禪的真境界。
5、問:禪宗主張「佛法不離世間法」的妙諦出自《維摩經》何處?如何說?
答:出自《維摩經、菩薩品》第四,維摩詰告訴光嚴童子說:「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波羅蜜是到彼岸的意思,也有究竟的意思。菩薩若能依照諸波羅蜜法相應自行化他,那麼,凡有所作的一切事,就如一舉一動,也無非是佛事了。這有即所謂「喜笑怒罵,無非佛法,行住坐臥,盡是道場」的一切智境界了。
對此,禪宗六祖《壇經•無相頌》說: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六祖這裡指的佛法與維摩居士所說的波羅蜜法是同一究竟,及佛所傳的一乘頓教之法。此法如何修得?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說:
「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愛憎,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正定);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覺果)。」
所謂「一行三昧」,就是指心專於一行而修習的正定。又叫一三昧,真如三昧,一相三昧,一相莊嚴三摩地。這一行三昧又分為二:
- 是「理」的一行三昧,是以定心觀法界平等一相的三昧。入這三昧就知道一切諸佛法身與眾生身是平等無二、無有差別的。所以在行住坐臥等一切處,能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如《大智度論》卷四十七說:
「一莊嚴三昧者,得是三昧,觀諸法皆一,或一切法有相故一,或一切法無故一,或一切法空故一,如是等無量皆一。……一行三昧者,是三昧常一行,畢竟空相應三昧中,更無餘行次第」。(大25•401中)
- 是「事」的一行三昧,即指一心念佛的念佛三昧。如《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說:
「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大8•731中)
修行的人只要照顧到「舉足下足」的功夫親切,若能依一行三昧之理事用心,時節成熟時便能當下悟道。世間出世間皆同此一心,本無二法,世間法就是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就是世間法,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迷為世間,覺即淨土,即所謂「隨其心淨,即國土淨」道理即在於此。
以前牛頭融禪師問四祖法要,四祖說: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起悲慮,蕩蕩無碍,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
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
據說融禪師從此得法後,法席昌盛。可見禪宗祖師傳承的「佛法不離世間法」,世出世間皆同此一心,本無二法,若執要離世間,另求菩提,就「恰如求兔角」。

6、問:禪宗也主張「一切諸法是解脫相」的理論根據何在?
答:根據《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第七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淫、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癡性,即是解脫。」
舍利弗在聲聞僧團中,智慧第一,但他只證空,不能涉有;只知道第一義空,離言說文字,站在第一義空的立場上就認為「解脫者,無所說」。而天女是站在真俗二諦並觀的立場上,就說「言說文字皆解脫相」。不必離開了言說文字另取解脫。因為解脫相是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的;也沒有時間性上的久近可言的,這種無相才能說解脫。如果解脫相有內、外、中間,就落在兩邊三處,這就不能成為無相解脫了。
文字相也是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三處的,因為文字雖然有相,而有相不離無相,無相不離有相。有相無相,理自平等,不成對立。如此文字相即是解脫相,不必離去文字相另尋解脫了。因為一切法都是解脫相,解脫相即是一切法,文字也是一切法之一,當然不必離去文字而另找解脫相了。由此可見,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只是唯恐學人拘泥於文字教相上所立的教示。
舍利弗從前聽佛陀說,離貪、瞋、癡也即離淫、怒、癡三毒才能解脫。現在聽天女說「一切諸法是解脫相」,那三毒也是一切諸法中的一法,這豈不是「不要離了三毒也叫解脫了嗎」?
增上慢是七慢之一,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即小乘人證到我空,以為得大涅槃。哪裡知道還有法執未除,法空未證,這種人就叫增上慢。
佛陀是曾說過離淫、怒、癡才能解脫,但是那是對下根的增上慢人方便的不了義說;如果對上根利智而沒有增上慢的人,佛就為他們說:「淫、怒、癡性(空)即是解脫」。使他們不必見有煩惱可斷,有涅槃可證。不使他們生厭離心,捨此取彼,生死涅槃成對待,墮於小乘,所以說淫、怒、癡性空,即是解脫,這才是大乘了義真實說。
《五燈會元》中有一個一切現成的公案,與此有同一意趣。
有一次,羅漢桂琛禪師問法眼文益禪師:「你曾經說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現在請你告訴我,庭院裏的那塊石頭是在心內,還是心外呢?」
法眼回答:「在心內。」
羅漢禪師便說:「你為什麼把這麼大塊的石頭放在心內呢?」
法眼被羅漢禪師問得無話可對了。從此之後,一直向羅漢禪師討教疑問,每天提出新的見解時,羅漢禪師都說:「佛法不是這樣的。」
最後法眼只得對羅漢禪師說:「我己經辭窮理絕了。」
羅漢禪師便說:「以佛法來講,一切都是現成的。」
聽了這話,法眼恍然大悟。
羅漢桂琛禪師所說的「以佛法來講,一切都是現成的」的「一切現成」是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說的。就如後來法眼文益禪師當了方丈之後就常對僧眾說:
「實體本來是現成的,就在你們眼前,可是卻被你們變為名相之境,你們要想想怎樣才能再回轉為原來的面目呢?」
如果不要把「佛性」變為名相之境,那麼「用」便是「體」。這就是「諸法皆如」的思想,也是突破體用界限的觀念。唯有「體用一如」才能達至「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境域。正如《維摩經》所說:
「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
禪的精神就是這樣超越體用界限的精神。正因為佛性無內、無外,石頭也是佛性所顯露的,有什麼心內、心外的界限分別呢?禪宗的「諸法皆如」思想即正符合「一切諸法是解脫相」的精神。
7、問:禪宗與三論宗一樣依教修觀,在修證上有個共同觀念,那便是「不可得處,怎麼得」的修證消息。這種思想根據何在?
答:根據《維摩詰經.觀眾生品》第七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
曰:「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天女追問舍利弗究竟有無證得阿羅漢道?舍利弗攝心反省後,才體悟到自己所證得的是無生道果,是不可言說的,於是回答說:「無所得故而得」。天女乘機破斥說:你證得阿羅漢尚是「無所得故而得」,「諸佛、菩薩」證得菩提「亦復如是」又何嘗不是「無所得故而得」呢!
小乘阿羅漢的無生道果和大乘佛、菩薩的無生道果,所證的程度本來有淺深差別,但所證的性質是相近的。譬如室內的虛空和室外的虛空本來有小大差別,但其虛空性質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小乘阿羅漢所證的偏空,因程度淺而不能涉有;大乘佛、菩薩所證的畢竟空,因程度深即能涉有。大小乘人的體用雖然有別,但證得之時是沒有兩樣的。所以天女即以小乘的無所得,來比大乘的無所得了。
我們可以從《傳燈錄》中舉一個公案來區別大小乘行人在修證上的不同消息:
一天,天皇道悟去問石頭希遷禪師說:「如果超脫定慧,請問你還想告訴別人什麼?」
石頭禪師說:「我這裹根本沒有奴隸,談什麼超脫?」
天皇不高興地問:「這樣的話叫人如何了解呢?」
石頭禪師不直接回答,卻反問道:「你知道『空』嗎?」
天皇答道:「我對『空』早有心得啦。」
石頭禪師說:「唉!不料你還是從『那邊』來的人。」
天皇抗議道:「我不是『那邊』的人。」
石頭禪師笑著說:「我早知道你的來處了。」
天皇說:「你怎麼毫無證據誣賴我呢?」
石頭禪師說:「你的身體就是證據。」
天皇問:「話雖這麼說,可你必須告訴我,究竟應該拿什麼東西來啟導後人呢?」
石頭禪師喝道:「請問:誰是我們的後人?」
天皇道悟豁然大悟。
南宗認為定與靜坐沒有任何關係,定不是寂靜也不是安靜。相反,定是活動,是行動,是見聞、思維、記憶。可以說,不行禪定的地方便得定,那定就是慧,慧就是定。禪宗自六祖以後所有禪師都強調「定慧一體」的主旨,所以天皇有意拿「超脫」二字來問難石頭禪師,既是「定慧一體」就沒有主客對待,既主客一體,就沒有奴隸,既無奴隸,當然都是主人,既然都是主人,又談什麼超脫呢?天皇不明石頭禪師的沒有奴隸,談何超脫深意,還停滯在知解上,石頭禪師便索性問他「空」義。正因為天皇不知道一法不立的畢竟空,才回答說:「我對『空』早有心得啦。」天皇所謂的「空」,若用修證上說,當然是小乘行人所證的偏空而不是大乘行人所證的畢竟空。所以石頭禪師才說他是從(小乘)那邊來的人。可是天皇不肯承認自己是小乘空宗,因此抗議說:「我不是(小乘)『那邊』的人」。石頭禪師所說的「空」是無所得畢竟空。在畢竟空中,沒有自他彼此分立,而天皇還有自他彼此對待分別。所以石頭禪師才說:「我早知道你的來處了」。可是天皇還不服氣,石頭禪師便以身體作為證據。有了如幻的身體,自然就有自他彼此之分;身體最後歸空,自他彼此也就不存在了。這時「請問:誰是我們的後人」?「定慧一體」即無自他,既無自他,即自他彼此一體,這自覺即是覺他,那裹還有後人呢?因此,天皇豁然大悟。
8、問:禪宗的「唯心淨土」、「直心是道場」思想出自何處?
答:一.《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說: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二.同經《菩薩品》第四也說: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直心是不彎曲的心,是修行證道的根本,所以《楞嚴經》說「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
「直心」和「不諂」是因;「淨土」和「成佛」是果。因為菩薩在因地時修行直心,到他成佛時,其果感得「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這裡或許有人疑問,菩薩以「直心」自行化他,那是自然,但如何能感得由他所化的「不諂眾生來生其國」,不能生到別的佛國嗎?
對此《義記》中作四點解釋:
「一.以直心淨業之力,自然還感彼不諂眾生來生其國;如屠殺人,自然感彼屠殺眾生來生其家。二.由自直心,令他直心眾生,樂見愛好親近,故令不諂眾生來生。三.自直教他,所教眾生還來歸從,故令不諂眾生來生。四.由直心得好淨土,以土好故,物(眾生)皆樂住,故令不諂眾生來生其國。」
三.同經《佛國品》第一又說:
「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這一段是「唯心淨土」的思想,淨土是由心識所變現出來的影子。所以說「若菩薩欲得淨土」只要心淨,淨土自然也就清淨了。好比人的影子隨形,形軀端正而不歪,那麼影子自然也就端正而不歪了,所以說「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是因果定律,也是報應的道理。唯心、唯識的學說,也是依此而建立的。也正是《華嚴經》所說的「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的道理。
這種唯心淨土的思想,《佛地經》也說:
「最極自在,淨識為相,故識淨時,佛土便淨。」
「一切唯心造」的造字,不是造作義,而是變現義。我們如果站在凡夫固有的情見立場來觀萬有,則萬有成對待;如果離開情見站在「直心」如實境的禪的立場來觀萬有時,則溪之聲,風之音,都是自己的聲音;松之青,柳之綠,無非都是自己的色彩。所以蘇東坡吟出「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的法界詩聲。
禪宗有一僧人針對這「唯心淨土」的意義,求教於黃檗禪師。
禪師說:
「心若清淨,何假言說。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語言,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須無漏。如今修行學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羅老子拷訊你在。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自然不照而照,豈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路,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你清淨法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黃檗禪師這段回答告訴我們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在得到絕對清淨的意識時,那便是清淨心。心若清淨,就意味著已經超越「淨」與「不淨」的二元對待觀念。此心如何才能得到清淨呢?只要「但無一切心」,無論在「行住坐臥、一切語言,但莫著有為法」將心「空」去,那便是清淨心。可是,如果你心若想要得到東西,那是有漏,此心又「不淨」了。只有「盡須無漏」在不考慮「淨」與「不淨」的時候,才會有「少分相應」絕對清淨意識。這「絕對清淨意識」,便是「自性清淨心」也就是禪宗所說的「自性」,若以自性來觀萬有時,一切事物無非「自性」顯現,如此有情、無情平等一如,沒有主客物我分別。對此,《傳燈錄》有一「無情說法」的公案正說明這層道理:
洞山良价初次見到雲巖禪師時,便直截了當地問:「無情說法時,誰能聽到?」
雲巖禪師回答說:「無情能聽到。」
洞山再問:「你能聽到嗎?」
雲巖禪師說:「假如我能聽到的話,我便成了法身,那麼你就聽不到我的說法了。」
洞山仍然不解地問:「我為什麼聽不到呢?」
雲巖禪師便提起拂塵說:「你聽到嗎?」
洞山回答:「聽不到。」
雲巖禪師便說:「我說法你都聽不到,更何況無情說的法呢?」
洞山又問:「無情說法出自何典?」
雲巖禪師回答說:「《彌陀經》中不是分明說:『水鳥樹木悉皆念佛、念法』嗎?」
洞山聽了這話,心有所悟,於是作了一首偈子: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這裏的「眼處聞聲」和日本百隱禪師以一隻手舉起教人聽出聲音其意相似,通常眼識所接觸的只是色塵,而不是自性的色彩;耳識所接觸的也只是聲塵,而不是自性的聲音,由於「自性遍一切處」所以洞山所說的「眼處聞聲」,此眼並非肉眼而是智眼(或稱心眼、正眼。何謂「正眼」?請看《禪宗思想問答》第九題)。只有具足智眼的人方能聽聞法界詩聲。
兩年前,新加坡政府發現該地沒了烏鴉,於是向外地買回許多,不料烏鴉繁殖甚快,百姓們一清早受不了烏鴉的哇哇吵鬧雜聲,於是政府又叫人槍殺烏鴉,這前後一愛一憎都是由於眾生的計度分別所造成的人為矛盾,如果能以自性上去體認烏鴉,那麼烏鴉的聲音與自己的聲音無二,因為自性是一體的,佛性是平等的。有了平等一如的觀念,慈悲心就出來了。如此,便沒有彼此對待分別,到這種「隨其心淨則國土淨」的清淨心境,你睡你的覺,牠叫牠的音,彼此不相防礙。假如你睡不著覺,一怒之下衝出房子,向著不同語言的異類烏鴉破口大罵,甚至迫不及待地叫人開槍殺死烏鴉,這種一愛一憎一喜一怒的前後矛盾行為,不叫淨土而叫「五濁惡世」了。
佛教不但認為一切有情識的眾生有佛性,而且主張無情識的山河大地也有佛性說。其實,無情是沒有佛性,也不會成佛的。之所以主張「無情有佛性說」是因為有情、無情都是佛性的一體。眾生之所以成佛是在佛不是佛時才是佛,如此才能達到物我一體;換句話說,能觀正報的色身與依報的山河大地平等一如才能稱其為「心淨」,可見這「無情說法」的公案正是告訴我們,「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的「淨其心」是必須超越主客對待分別,這種超越主客對待分別的「無分別」就是於色、聲、香、味、觸、法六處無染污心。這種「無心」就是禪宗的根本宗旨,也是本題「唯心淨土」、「直心是道場」的思想理論體驗。
9、問:禪宗的「娑婆即淨土」的思想根據何處?
答:根據《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在此之前,佛陀把「心淨則國土淨」的道理說完了之後,舍利弗開始起了懷疑,所以才有梵王向舍利弗解釋淨和穢的定義:「仁者舍利弗!你見此土石諸山高低不平,充滿穢惡,那是由於你自己的心不清淨,心有高下所致!你們聲聞人不依佛陀平等深慧,只是停留在狹劣的智慧在分別諸法的染淨、高下、平等差別、空有、罪福、善惡、男女、苦樂等對立概念,所以就看見這娑婆國土是不淨了。
舍利弗!菩薩是依於佛的無分別平等智慧,觀見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菩薩清淨的眼光來看山河大地,便無非是佛的淨土了」。
禪是非常現實的。因此,禪注重當下:不迷戀於過去;也不執著於未來。更不將死後的世界當成目標去努力,而是不斷地去體驗當下。只有當下才是最真實的。當下即是直心,直心則看娑婆即淨土。禪不認為有定性的苦或定性的樂;換句話說即不分苦樂界線,也即無苦無樂的無界線分別;一有對立分限, 就不是禪了。
所謂「娑婆即淨土」只有打破了空間和形像的對立界限觀念後,才是真正超越的禪者,否則也只是一種知見而已。正如《傳燈錄》有一「何謂正眼」的公案可以說明這一道理。
有一次,趙州禪師想去山西五臺山文殊菩薩的道場──清涼寺。
有一位學禪的人聽說趙州要去朝五臺山清涼寺,便寫下一首偈子遞給趙州禪師。
「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需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
趙州禪師反問一句:「何謂正眼?」
學禪的人無話可對,於是趙州禪師依然前往。
學禪的人認為佛的法身是遍一切處的,只要我此心地道場清淨如帝珠,佛就能感應道交,又何必一定要拘泥於空間和形像,非去五臺山清涼寺朝拜不可呢?趙州禪師早知作偈的人著落在青山、道場、清涼、金毛獅子、正眼等名相概念上,這只是一種知見,所以趙州禪師才反問他:「何謂正眼?」正因為作偈的人無此正眼,才無言以對。一個具有正眼的禪師,當然不會被時空和形像所限制,但也不會否定時空與形像的存在,這才是真正做到不戀過往;不著未來,注重當下眼前,該做什麼便做什麼;該去五臺山便動身前往了。
10、問:禪宗認為眾生的法身不可說;法身遍一切處;法身是「動靜一如」等思想有何依據?
答:依據《維摩詰經.問疾品》第五: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
維摩詰知道文殊等人來訪,為什麼空其室內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臥呢?正因為法身不可說,「空其室內」是暗示他自己分證常寂光淨土中;疾身是表示正報的法身;「床」是代表依報的法界。正因為法身是遍滿法界的。「以疾而臥」來暗示疾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處;同時也暗示著,如果大眾起了淨土與穢土的形像寄情分別,那仍能存在著法身之病;若能打破空間與形像觀念,就能體達疾身即法身,「娑婆即淨土」。這是維摩自己空其室內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臥的本意。
文殊師利走入維摩詰丈室,見其室空,便知道維摩以空室待賓的用意。這「室空」暗示著真空,「獨寢一床」暗示著妙有,真空非空,妙有非有,非空非有便契入中道。中道不可言詮,開口即錯,動念即乖,所以文殊不先開口;但維摩也知道文殊早證常寂光淨土,已領會空室本義,也就以主人的資格先開口說:「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維摩與文殊同證一法身,同證一中道實相理體,今天是他們顯身說法的機會了。維摩是主人猶如體;文殊是賓客猶如用。體用一如,從體起用,主在賓先,那當然是維摩先開口說話了。所謂「善來」是讚嘆文殊師利不動寂光淨土而來此處。寂光常寂不動,本無去來相,因為法身的體是絕來去相的。維摩所說的「不來相」正是顯法身理體而言。既然體絕來去相,即「法身體絕名言」。「法身不可說」的道理就在這裹;「而來」是顯從法身體生起妙用。「不見相」是說寂光常寂無相可得的;「而見」是說從不見中而有見,此「見」非一般凡夫的妄見而是菩薩的真見。真見是見無相而無不相,也就是證無為而無不為的從體起用作略。
文殊師利聽到維摩一句話後,即刻印可說「如是居士!」法身本是如如不動遍滿一切處的,若說有來去相,即成有彼此對待,有對待就有方位處所,有方位處所就有來去二相,有來去二相就不能成其為法身;因為法身是遍滿法界的,既遍滿法界的法身雖動而常寂,這叫動靜一如,所以不能說法身有來去相。為什麼呢?因為若是來的,就已不是來了。時間不出三世,可以這麼說:「已來亦不來,未來亦不來,離已來未來,來時亦不來。」已來的來相早已過去了,未來的來相還未至,離開了已來和未來,就是來時的來相亦不可得。來既然是這樣,去亦如是。所以說:「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因為來去是相對的,既無所從來,當然也無所去了。還有什麼可以說來去相呢?既無來去之相,也就沒有有見無見了,如果見已更有見,就落在有能見者和所見者,有能所即成彼此對待,有彼此對待就不是菩薩的真見而是凡夫的妄見了。真見是絕對的,絕對的真見不帶見相是一見不可再見,再見即是妄見,若是凡夫之見是帶見相,帶見相之見就叫妄見,妄見只見疾身不見法身。「不見相而見」的真見道理出自《楞嚴經》有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對此法身與知見問題,《五燈會元》中有個「示主沙彌」的公案正表示這一道理。
仰山還是一位沙彌的時候,一天去拜訪溈山禪師,溈山禪師問:「你是有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
仰山回答說:「有主。」
溈山禪師又問:「主在什麼地方?」
仰山從西走到東,然後立定。
溈山禪師深為賞識,於是垂加開示。
溈山禪師所問的「你是有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的「主」,在此可以說指的是「法身」。偽山禪師聽到仰山回答說「有主」之後,唯恐仰山只是「知見」上的法身,因而緊追著問:「主在什麼地方?」仰山知道法身是遍滿法界的,不可說在什麼地方,在法身面前開口即錯,動念即乖,所以他不肯開口是用行動來表示,於是「從西走到東,然後立定」,以說明不可說的法身,然法身又是「動靜一如」的。這一則公案充分暗示了法身不可說,法身遍一切處,法身是動靜一如的,這公案與前面經文大意正好吻合。

11、問:禪宗的「默識心通」的無言妙用根據何在?
答:根據《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對此,羅什法師講了下面一個故事:
「自佛泥洹(入般涅槃)後六百年,有一人年六十出家,未幾時頌三藏都盡。…思惟言,佛法中復有何事,唯有禪法,我當行之。於是受禪法,自作要誓,若不得道,不具一切功德,終不寢息,脅不著地,因名脅比丘。少時得成阿羅漢,具三明(一.宿命智證明,二.生死智證明.三.漏盡智證明)六通(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有大辯才,能論議。有外道師名馬鳴,利根智慧,…聞脅比丘名,將諸弟子往到其所,唱言:一切論議,悉皆可破,若我不能破汝言論,當斬首謝屈。脅比丘聞是論,默然不言。馬鳴即生憍慢,…與其弟子捨之去。中路思維已,語弟子言:此人有甚深智慧,我墮負氣。…即下髮,為脅比丘作弟子。」
「默然無言」即「默然不言」,簡稱「默理」,即指「默然無言的妙理」。或稱「默不二」,即文殊菩薩等三十二位菩薩與維摩詰居士談論有關入不二法門的問答。其中,諸菩薩對生滅、我我所、受不受、垢淨、動念、一相無相、菩薩心聲聞心、善不善、罪福、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生死涅槃、盡不盡、我無我、明無明、色色空等相對原理,各提出超越此類相對問題的答案,而以是為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則認為「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面對文殊等諸菩薩的詮釋,唯獨維摩詰居士默然無言,即「默不二」,無言以對,才能真正顯示入不二法門的最高諦理。禪宗就是根據這一默然無言的妙用建立「默識心通」的禪機。
維摩的默然無言,遂為文殊歎為「真入不二法門」;而脅比丘的默然不言,也使馬鳴成為印度佛教史上最初興起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之一;禪宗的「默識心通」也使多少凡愚成佛作祖。這種無言妙用實在是不可思議!
12、問:禪宗認為要達到「自在無礙」、「徹見本性」、「法我不二」、「人法不二」以致於現實地打開常、樂、我、淨的涅槃四德心境,必須是對「無」的體驗,也就是自己的根本意識,從差別而進入平等的體驗,然這種體驗必須對於「法」或「真如」的把握,而這「法」或「真如」是不能形相加以把握的,這就是對「無」的體驗。這種「無」的根本指導思想出自《維摩詰經》那一段話?如何解說?
答:出自《維摩經˙弟子品》第三: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言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大14、540上)
這一段話,是維摩詰對目連向諸居士說法一事作了批評,認為目連未能從實相上來說,所以斥他不如法說。為什麼呢?因為,目連是聲聞乘人,他在說法前不曉得先觀察眾生的根性,只知道把自己所曉得的小乘法向白衣居士說,不知道這些居士是大乘根性的人;再說聲聞乘人多不明諸法的「法性」而妄執諸法的「法相」,心落有無二邊,不明中道。因此,心生迷惘,目連尊者所迷惘的「法相」,不出眾生相、我相、壽者相、人相四種,這四相是一切法相的總相。所以,維摩一開頭先教他離此四相。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所謂「眾生」,就無情事物方面說:是指一切法皆由眾多因緣和合而生的叫作眾生;就有情動物方面說:凡是從胎、卵、濕、化的四生六道的眾多類別出生的也叫眾生。眾生是由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而生,其性本空。如《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而眾生妄執五蘊為實有,結果造種種惡業,由惡業因緣就有垢穢,由於垢穢染污不得清淨,所以從「法相」上說「眾生垢」;若是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就沒有實在眾生可得,菩薩已「度一切苦厄」便不造種種惡業,自然遠離眾生垢染。菩薩見五蘊諸法本性畢竟空即見法性,見法性即見中道。如《心經》說:「舍利子,是(五蘊)諸法空相(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這種「空觀」之智便稱為「無所得之智」,而無所得之智就是「般若」;於此相反構成相對差別概念經驗之智則稱為「有所得之見」。凡夫二乘都是停滯在這「有所得之見」而不能如菩薩照見「諸法實相」,因為只見得「法相」不照得「法性」的緣故。
「法無有我,離我垢故」。凡夫執著這地、水、火、風四大和合的色身為我相。這樣就有我執、我見、我慢、我愛等我垢相;聲聞雖然證到我空,但還尚存有能觀的人,所觀的法,這樣還是有我垢相;菩薩見到無我諦理,證了我與無我之理不二,不再妄執有個自我,我自本空,當體無我,沒有能觀的人也沒有所觀的法,這樣就自然離我垢了。
「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所謂「壽命」就時間性說叫「壽」;就連持性說叫「命」。如人生在世活到六十、七十、八十、九十歲的稱其為「壽」。在這一期生命當中,身心連持和合成為完整的生命體,就叫「命」。然這一期的生命,是從生到死說的,所以有了壽命,就一定有生死,這一期命終,死此生彼,這就是生死相。
聲聞乘人厭離生死,以為有涅槃可得常住,證涅槃也就成了聲聞乘人的壽者相,既然有壽者相,就必然有生死相。這正是聲聞乘人偏空急於取證的涅槃,這種涅槃不是究竟的涅槃。
菩薩證得法性本來空寂不昧生死超越時空觀念,過去是無始;未來是無終,生是幻生;滅是幻滅。所以,菩薩洞察在法性空寂中無壽者相可得而離生死的。
「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一般認為前際已經生起,後際還沒有消滅,在這中間所生存著的身體,這就是人相。那為什麼說「法無有人」呢?這是菩薩觀察法性本來常住不動的。這裹的「本來」與時間沒有關係,所以說法性常住不遷,因為法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的。「無所從來」是說法性從來不生;「亦無所去」是說法性從來不滅,這叫「有佛無彿法性常住」。這樣就沒有已經生起的前際相,也沒有消滅的後際相,既無前後際相,那中間賴以生存的人相自然也就無存了。
「法常寂然,滅諸相故」。菩薩了知諸法本性也即「法性」常住寂然。正如《法華經》說的:「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這法性也就是實相,而這實相本來無相,這實相無相之法性又無不相,所以菩薩不著有相;也不著無相,如此才能離諸相證中道,菩薩證中道是不證地證。
二乘聖人要滅了有相證取無相,這樣才能得到寂滅相的涅槃。可是二乘聖人不知滅了有相還停滯在無相中而仍然未能離開執著,不能滅諸相,不能離相則不能成佛。
「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所緣的「緣」是攀緣的意思,心識所攀緣的境界叫做「所緣」。菩薩不住著法相,因為菩薩了知法相即法性,由此轉識成智,達到心對法無所攀緣的境界;聲聞乘人雖然得到我空,但還停滯住著我空之相,所以不能達到無所攀緣的境界。
「法無名字,言語斷故」。菩薩破了我執,了知法性寂然,所以能夠離名字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有所謂「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名字相」;聲聞乘人法執沒有破除,不能離開從妄想心所生的語言和名字。
「法無有說,離覺觀故」。粗的尋思分別名為「覺」;細的尋思分別名為「觀」,這種覺觀都能擾亂禪定的心。法性是超過了尋思分別的覺觀境界,所以法性不可宣說。就佛陀宣說的法性也只是強設名言概念的名相法,而不是離言無名相的真實法,可是聲聞乘人墮在粗細尋思分別的覺觀中,自以為修習禪定;菩薩了知法性不可宣說,離了覺觀粗細尋思分別,既離覺觀,自然也就離言說相了。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聲聞乘人雖然不著人相,但是還是執著法相,以為有染相可離,有淨相可修,有道相可證,於是就停滯在離相、滅相、斷相中而不能自拔;菩薩了知法性平等,本無差別,猶如虛空一般,不可分析,何來的可離、可滅、可斷、可修、可證等的形相呢?
「法無戲論,畢竟空故」。凡夫和聲聞執著諸法是有的,是無的;是染的,是淨的;是常的,是無常的;是一的,是異的;是來的,是去的,如此等等所有名言都是落於戲論分別;菩薩了證法性畢竟空,不著法相,了知法性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在諸法畢竟空中,那裹有生滅、斷常、一異、來去相的言思分別呢?所以菩薩於諸法畢竟空中,離有、離無、離亦有亦無、離非有非無等四句,斷言思、絕百非,於諸法上無諸戲論。
「法無我所,離我所故」。聲聞乘人斷了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等五種不正見的「見惑」;同時又斷了貪、瞋、癡、慢、疑等五種煩惱的「思惑」證阿羅漢果,出離三界。但對於諸法不能明了,以為有我所修、我所證,所以聲聞乘人雖然破了我,但仍未能除我所;菩薩了知法的本性是空,在畢竟空中,既無色、無受、想、行、識的無「我」可得,那裹還有「我所」可得呢?所以菩薩不但能破我,同時又能除我所。
「法無分別,離諸識故」。聲聞乘人還沒有證到無分別智,所以還是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色聲香味觸法六塵而起虛妄分別,分別四諦中的集諦是世間因,苦諦是世間果。道諦是出世間因,滅諦是出世間果。他們只知道世間因果現象,逃避世間,欣取涅槃,得了個自了漢,不能入世弘法利生;菩薩證到無分別智,不依妄識而起分別,觀四諦諸法,其性本空,證「無苦集滅道」,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世間、出世間等不成對待,無二無別。這樣才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才能做到「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薩大弘誓願。
「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聲聞乘人的觀法是生滅取捨的觀法,這種觀法是相待的而不是絕待的,相待的觀法就叫「比觀」。比觀「有」,才能觀「無」,比觀苦集二諦,才有道滅二諦;菩薩了知諸法不生不滅,這是無生滅觀,是不取不捨的觀法。這種觀法是離能所相待,是絕對待的觀法。這種觀法就沒有比對可得的,是無相待的。
「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性不屬於「因」。為什麼呢?親生的叫作「因」,疏助的叫作「緣」。譬如種子有陽光雨露的緣在,才能說種子是屬於「因」,可是種子本性空寂,本性不在陽光雨露的緣中,所以說法性也不屬於「因」的了。這正是顯明聲聞乘人要以因緣來分析觀察後才可以修道證果的;菩薩就不是這樣的,菩薩了知諸法當體即空,不待廣作分析。菩薩的修道證果是修而不修,不修而修,證而不證,不證而證的。
「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所謂「法性」,就是諸法的本性,也是諸法的自性。這裏的「入」有「順」的意思,也就是說聲聞乘人所證得的理是偏真的,這偏真就不是中道諦理。所以他們以為法有染、淨之分,也就順於淨不能順於染,順於涅槃不能順於生死;菩薩所證得的諸法本性常自寂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因此,在諸法畢竟空中,何來的染淨對待分別?何來的生死異於涅槃?這就所謂「一法順於一切法,一切法順於一法」;也就是《華嚴經》所謂「一入於一切,一切入於一」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華嚴會上菩薩境界。
「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所謂「如」就是如如不異的理體,也就是「一如」的意思。法界中的事相雖有千差萬別,但法界的理體是如如不異的。聲聞乘人對於事理不能相隨,入定才能觀理,出定只能觀事,理事不能隨於一如;菩薩證入如如不異的理體,從體起用,動靜不二,體用一如,理事也能一如,入定觀理無礙於觀事,出定觀事不礙於觀理,既然能理事一如自在無礙,那再也無可隨了,這種隨是無所隨的隨。
「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所謂「實際」,是指真如實相的理體。「諸邊」是指有邊、無邊、斷邊、常邊、染邊、淨邊等等邊見。聲聞乘人見有生死可以了脫,即落有邊,見有空可以取證,即落無邊;菩薩證得真如實相理體,了知真空非空,妙有非有,非空非有即是中道,所以菩薩不落諸邊,不為諸邊所動。
「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二乘聖人雖斷見思二惑,證阿羅漢而出離三界。但還沒有通達如塵如沙的無量法門,不通無量法門,就不能完成教化眾生的弘法利生事業,所以還有「塵沙惑」和「無明惑」。這「無明惑」最為根本,能障蔽中道實相諦理。因此,二乘行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心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境時依然還會隨境動搖不定。然這塵沙、無明二惑也是菩薩的惑,菩薩也必須斷盡此二惑才能成佛。維摩居士早已成佛,當然無此二惑,今生化現娑婆只是助佛弘化,現居士菩薩身而已。若是第八不動地以上的高位菩薩見六塵境當體即空,同一法性,明了六識虛妄分別,即見清淨本性,所以菩薩見「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如此即能安住於真如法性中,不為六塵所轉動。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小乘法有去有來,有從去三界生死,有來證出世涅槃,以為涅槃常住,認為涅槃是「變的終止」。他們不知道雖然斷了三界內有身分形段可見的坐死輪迴──「分段生死」,但還未斷除三界外心念精神上生滅不停的──「變異生死」。既然還有變異生死未除,那就不能說是常住的了;菩薩斷除根本無明,才無「變異生死」,無「變異生死」才能真正常住,為什麼呢?因為菩薩了知法性空寂,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大乘是「無去亦無來」的。無從去三界生死,無來證出世涅槃。這種涅槃是不住而住,不證而證,常無有住,才是真正的常住。法本無去來,如果作去來想,心起常住念,其實這是精神上的生死,這本身就是「變異生死」,何有常住可言?
「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這裏的「空」、「無相」、「無作」(又名無願)是三種三昧,叫「三三昧門」。三昧是定的意思。空三昧是觀察世間一切諸法都是緣生的,也都是虛妄不實的;無相三昧是觀察世間一切形相都是虛妄假有的;無作三昧又名無願三昧,是觀察一切法幻有而無所作、無所希願與追求,所以這「三三昧門」又叫「三解脫門」。
法性既順於空理,自然也就隨於無相,既然隨於無相,自然也就應於無作,這裏的「應」是隨順的意思。順即是隨,隨即是順。聲聞乘人也能修習「三三昧門」,但他們只有在入觀的時候,才能做到「空」、「無相」、「無作」三門隨順相應,出觀的時候就辨不到了;菩薩能圓觀自在無礙,雖觀諸法相,但又能順於法性空理,隨於無相,應於無作。
「法離好醜」。小乘行人但見法相,不見法性。但見法相有千差萬別,所以有好、有醜,這是妄想分別心造成的,有了好醜就有染心分別對待。如小乘厭離生死欣取涅槃,說生死是染的、是醜的,涅槃是淨的、是好的;菩薩見法性平等一味諦理,就沒有好醜染淨分別對待了。如禪宗四祖道信祖師說:「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這是「法離好醜」的最佳寫照。
「法無增損」。小乘行人但見法相差別,不見法性平等,所以心存揀擇,把隨順利益的法增益起來,將違逆惱的法減損下去;菩薩見法性平等,本無增損違順差別,所以其心也就平等,不存揀擇,不生增減分別妄見。
「法無生滅」。小乘行人但見法相生住異滅,心存生滅觀念;菩薩見法性不生不滅,法性天然、法爾如是、法本空寂,其心不存生滅知見。
「法無所歸」。小乘行人認為法相的義理有「分齊」,所謂「分齊」就是指界限差別,也就是指內容、範圍、程度上的界限或差別。一有「分齊」就會將此法歸於彼法,或將彼法歸於此法;菩薩見法性遍一切處,對法相的義理就沒有「分齊」,所以也就無所謂歸與不歸的問題了。
「法過眼、耳、鼻、舌、身、心」。小乘行人執著於色、受、想、行、識五陰,又著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又著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的三科法相,由於執著法相,為法相所限,不能超過六根;菩薩了達法性無相,不著法相,不為六根六塵形相所限,超過六根六塵,所以菩薩不為境緣轉,又能轉境緣,在在處處,自在無礙。
「法無高下」。小乘行人但見諸法形相,所以就有大小、長短、方圓、高下差別不等;菩薩通達《金剛經》所說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義理,了知法無高下差別等形相。
「法常住不動」。小乘行人觀察事物用的是生滅觀,於是看這個世界就有成住壞空的生滅形相,此種觀法,雖破「常見」,但又執為「無常」;菩薩用的是無生滅觀,見法性如如常住不動,那成、住、壞、空的變動只是法相的生滅。
「法離一切觀行」。小乘行人只能看到諸法的義理教相,用妄識去推測,所以有能觀的功行,有可緣慮的塵境;菩薩了達諸法當體空無自性,與「法」爾真理相契合,如此既無能觀的功行,也無可緣慮的塵境,自然也就「離一切觀行」了。
13、問:禪認為「法身」是不病的,感覺有病痛是生滅法的「色身」。若能超越形象的覺受,病就不影響「法身」的自在。禪宗祖師對此有何垂示?有何經典可以說明這一教示?
答:德山禪師將臨終時,有人問他:「是否有永遠不病的人?」他回答說:「有。」這人又問:「如何才是永遠不病的人?」他叫著:「啊唷!啊唷!」
德山禪師以「啊唷!啊唷!」來回答提問者,其意暗示只要有色身就沒有永遠不病人;要想永遠不病,就必須證得法身,只有法身才是永遠不病的人。因為有色身形體,免不了有生滅病痛現象;假如證得法身,超越了形像的覺受,病痛是不影響「法身」的自在,這法身便是永遠不病的人。
現就《維摩詰經˙問疾品》第五,文殊師利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這裏,文殊問維摩詰三個問題:1.這疾病是從什麼原因生起的呢?2.生起多久了呢?3.怎樣才能將病除滅呢?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則我病滅。」
菩薩證得法身本來是沒有生滅的,然菩薩為悲愍眾生,示現人間度眾生流轉生死,有生死就有病痛;再者,菩薩粗的分段生死和變易生死已經斷了,但還有細的變易生死未斷,所以不免有病痛,這就是:「從癡有愛,則我病生」的意思。
那麼,菩薩的病生起多久了呢?所謂癡,是我癡,也就是無明,從我癡而有我愛,有我愛就有我貪,有我貪就有生死流轉,因此,這病是從無始以來就生起了。 菩薩是因為一切眾生病,所以生病,如果一切眾生不得病了,菩薩的病才算滅。但事實上眾生是無邊的,無邊的眾生菩薩是要誓願度的,所以,經文接著說 :「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
只要有色身形體的,都免不了生老病死的因果定律。所以,再去看野狐禪的公案就容易多了,有人問一位方丈:大修行的人還落因果嗎?就因為方丈答:「不落因果」,結果墮野狐身五百世;後因百丈禪師作一轉語說:「不昧因果」,那方丈才脫離野狐身!為什麼呢?因為所謂的不落因果等於不落生死,只要有色身就有生死,有生死難免不病!要想不病就要大修行,唯有在因果生死流轉中不昧,常以法身見如來,才是永遠不病的人。
14、問:真如有隨緣與不變二義,禪宗在真如二義上重視什麼?禪宗祖師如何教示?有何經文可以證明?
答:禪宗在真如二義上重視隨緣,因為怕學人著空,所以常從用上立說。有時就體上說,也怕人著有。如有一位三藏法師問大珠慧海禪師:「真如有變易嗎?」禪師說:有變易。三藏說:「禪師錯了!」禪師卻反問說:「三藏有真如嗎?」三藏回答說:「有。」禪師說:「若無變易,三藏決定是凡夫僧了。」三藏說:「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禪師說:「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三藏說:「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得當?」禪師說:「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說:「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若說不變易,那是真如之體;若是真如之用,那是無時不變。所以,真如有隨緣與不變二義。隨緣是真如之用;不變是真如之體。有所謂真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真如雖隨緣而不變,所以說:「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真如不變而隨緣,所以說:「本自具足,能生萬法。」這正是大珠和尚說的「若了了見(不二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
對此,維摩詰經說:「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便是真如不變而隨緣的經證。同經又說:「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也是禪宗重視隨緣之精神所在。
<目錄頁>
Webmaster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olorado
8965 W. Dartmouth Place. Lakewood, CO 80227
Phone : +1-303-985-5506 Email: baocden@yahoo.com